難得二人站成一排合照(喂好像是你在偷拍的吧)
站在皇帝身邊的小桂子難得的純良可愛呀哈哈哈哈哈哈(毆飛)
--------------------------------------
今天是三月十八。
早在半個月前,韋小寶攜著雙兒,騎著馬走出了揚州城,划舟渡過了江河,輾轉來到屹立在平原上的宏偉城門前。
守在關口的清兵輕易被他倆的易容騙倒,放了這名五年來一直被下令通緝的朝廷要犯。他們的易容術在這幾年間練得爐火純青,只因韋小寶本來就不是一個會滿足於安坐府中喝茶嗑瓜子的
人。
尤其是,愈近三月,他便每日都寢食難安,看見他這副模樣,娘親和六位老婆都不明就裏。
除了雙兒。
「相公,您是不是想回京城看一下?」
這一年,三月初一那天,雙兒主動問出了這句話,他怔了怔,咧出一抹笑。
也難怪,幾年以來,每逢三月,他便會帶著雙兒離府,為免另外七位女眷擔心,他還編好了
藉口,說是要到處遊山玩水一下。
「還是我的好雙兒了解我。趕快收拾好行裝,咱們今晚就離開揚州城。」他趁雙兒不設防親
了一下她的臉龐,惹得她滿臉通紅地跑開。
有時候他也會想,每一年都做的這件事,到底有什麼意義可言。
是無意義。
可是,就算是這樣,逢到了三月,他就會樂此不疲地收拾起行裝,溜出揚州,出發來到可以看到某個人的身影的京城。
會帶著雙兒離府,不止是因為他由衷喜歡著這位老婆,更是因為她體貼得不會向他好奇過問任何事情。
不過,如果雙兒真的問起他每年三月回京的緣故,他也不知該如何回答她。
直接說,因為他想念皇上,所以想回京看看他嗎?
即使他與皇帝是從小到大膩在一塊的好兄弟,也不會想念得要這樣頻密地一年回京一次吧?
這樣回答,鬼才不會引人懷疑,雙兒又是個聰明細心的姑娘,她一定會發覺些什麼的。
難以想像當雙兒發現了這個他一直隱藏於心的答案,她會有何反應。應該會很驚訝吧?
他自認對某個人的想念收藏得非常隱密,白晝的時候,他陪伴娘親老婆,追打偷跑出去賭錢
的虎頭的屁股,揪著銅鎚的衣領把他帶回書房練字,端來清水為雙雙洗去她臉上塗得像猴屁股的胭脂,還有拿出骰子決定是夜陪伴他睡覺的人。
晚上,當枕邊的嬌妻沉沉睡去,他躺在床上,對著縱橫的房樑,複習著以往的日子,那些與某個人一起渡過的零星片段。
完全是不由自主的。
十五年前,曾經有一個不能算是吻的吻,咬破了他的嘴唇,他撫上唇間,血痕早已消失,可是他無法忘記。
那標誌著,他忠於天地會,同時又不能捨下那人的矛盾行為,還有那人難得大發雷霆的證據。
那一咬,卻強而有力地撕扯下他偽裝的嘻皮笑臉,在歸氏夫婦二人揮劍刺向那人的時候,他像在清涼寺那回般撲過去,直至歸氏一家三口被侍衛亂刀砍死,他才踉蹌走開。
眼淚不受控制地流下來。
差一點,再差一點,若他動作不夠敏捷,就來不及了。
「今天,算你又贏了朕一注。」
那人說著這話的時候語氣很冷,許是洞悉了他過於強烈的反應下的情感。在那時,他終於明
瞭,自己不得不走了。
到了通吃島,每天逍遙自在地過活,七位老婆形影不離的伴在他身旁,這樣神仙般的生活,夫復何求?
「小桂子,他媽的,你死到哪兒去了?老子很想念你......」
聽著宣讀聖旨的尖細嗓音,看著地上一字排開的六幅畫,他眼淚滴在宣紙上,暈開了被壓在地上的小孩的臉。
原來他不滿足。
一直以來他都不滿足,因為通吃島上,沒有那個人頎長的影子。
「......我就快大婚了,你不回來喝我的喜酒,老子實在不高興。」
他的淚僵冷在頰邊,那些畫上的十多張臉龐同時咧開了嘴,他才恍然大悟,開懷的笑弧是緣自對他的嘲弄。
「趙大哥,請你回去後向皇上稟明,奴才忠義不能兩全,只好來世再回京服侍皇上。」
他這樣對趙良棟說,心中很是不痛快,令他連一個笑容都擠不出來。
誰要回去喝那人見鬼的喜酒,誰要回去看著那人在佈置得像掛了滿殿麗春院姑娘的大紅肚兜般的太和殿裏,迎接那頂紅轎上的女人。
雖然他知道,自己的氣憤來得全無道理可言;那人乃當今大清皇帝,怎能不娶后納妃,產下子嗣。
他沒有回到中原,一年復一年過去,吳三桂之亂平定了,鄭克塽投降了,台灣被納進大清版
圖了,聖旨無間段地每年傳來,不知何時不再言及滅天地會。
每傳來一道聖旨,他的爵位便會又高了一級,從三等爵到一等爵,從通吃伯到通吃侯,他很清楚,那只是某人用來牽制臣下的手段。
十年後,他最終按捺不住島上單調的生活,施計讓施琅把自己和夫人兒女們迎到台灣,然後
自台灣回到京城。
真正捺不住的,是思念。
他對著自己,承認了這個事實。自我欺騙是一件痛苦的事,他韋小寶是打死也不肯幹的。
本來以為他可以控制,他能夠藏起自己的情緒,帶著笑跪地頓首,恭恭敬敬地向那人喊:
「奴才韋小寶叩見皇上。」
最後的幾個字變了調,笑不出來,喉嚨梗得發疼,他額頭貼在地上,任由淚水浸潤光可鑑人
的石地,連身體,也是無法自己地顫抖著。
他媽的。
「他媽的,怎麼一看見朕就哭成這樣......」
他真的以為,這輩子他再長壽,也不能再見到站在面前的這個人了。
意外地看著那人伸來了手,雖然那張臉還是非常冷硬,他還是搭上了那隻手,被那人一把拉起來。
說到底,兒時的兄弟情,是依然存在的吧。
可他對那人的兄弟情,早就已經被掉包了。
他的眼淚,那人永遠也不會明瞭。
二更,韋小寶悄然自床上坐起,輕手輕腳地找來包袱,翻出一套侍衛服和官帽,在黑暗中穿戴好。
多年前已不再穿在身上的衣服有些不稱身,他側首看了仍然好夢正酣的雙兒一眼,悄悄拉開房門。
溜出了客棧,他壓低了頂上的官帽,在冷清的大街上,直朝皇城奔去。
早在五年前,為了方便潛入皇宮,他特意向雙兒討教輕功,可惜他之前不曾習過內功,無法
像師父、洪教主、胡逸之他們般飛簷走壁。
有些挫敗,可是他沒有想過就此打消入宮的念頭,畢竟他雖學不會輕功,但計謀還是有的。
況且,五年皆是如此,駕輕就熟。
走到害門前,守門的清兵沒有多問半句便打開了門,他知道那些士兵都喝過了酒,警誡鬆懈不少,方便了他潛進宮中。
這是他選擇在此時入宮的原因。
他放輕腳步,循著自身記憶走到乾清宮外,繞過了門前幾名正在打嗑睡的侍衛,賊頭賊腦地躡足,探至一扇窗前,蹲了下來。
他知道那人一定在這兒,雖然他不明白為什麼那人總是不翻牌子召來妃嬪,寧可自己一人睡在那張大床上。
韋小寶伸舌舔了舔食指,點在紙窗一角,輕易挖了個洞,把臉湊上去。
----------------------------------------
......出本的文停留在第十章中段orz
可是快要考試了,然後功課又突然多了很多= =某太的功課實在很不想做,可是我又不想因為這個被扣操行= =後天的《前赤壁賦》還有《三國演義》測驗我還沒有溫好,不如就放棄吧(毆)
最多不再YY軾轍和關張還有劉備X諸葛亮了,這樣東坡先生或許會保祐我XD(天:你想的美=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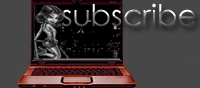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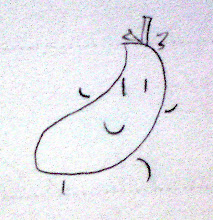


0 留言:
發佈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