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簾下覆蓋著的睫毛不算長,但很濃密,細看之下還能發現眼下一抹與睫毛形狀相近的暗影。
嘴唇顯得比平日更紅,有些微微腫起的感覺,看得他呼吸有點急促,環抱著赤裸腰肢的手臂圈得更緊。
這種情景,他已經看了很多年,卻從來不為此感到饜足。
一直以這種關係這種互動來維繫對方,他知道兩人之間,始終隔著一個胡維慵,但他也在很久以前就說服自己,這樣比完全沒有關係來得好。
高中至大學,從大學畢業後投身社會工作,他不曾遠離那曾經背對著他、背著台上燈光低吟淺唱,瞬間奪走他視線的身影,也擺脫不了自那時就已深植在心中的感覺。
那人對每一個九市一中的校友而言,都是個耀眼的人物,無人能對他視而不見,也因此,當年的他招惹了不少仰望著他臉紅尖叫的學妹。
那人的人緣也一直很好,班裏班外有不少朋友在中午時走進來把他拖去吃午飯,連只是一個旁觀者的他也覺得,交際應酬幾乎成為了那人的副職。
在得知那人竟然喜歡上阿慵的時候,他有好一段日子都避開那個人,不再在後頭默默向前看著那頎長的背影。
阿琰是個同性戀……他喜歡阿慵……
那還是阿琰親口告訴他的。
有種被欺瞞的感覺使他不知道往後應該如何面對那人,唯有獨自在暗角打造一副冷靜坦然的面具,忍著漿糊黏在臉上的不適將那能夠保護自己的面具戴上,當時他還不知道,待他再度接近那人的時候已不想再離開,任藏在面具下的本來面目悄然腐爛。
想不起那張富有生命力、隨著自己心情而變化的臉龐是何等模樣。
但大腦深處對那本來面目卻是記憶猶新,於是,他開始學會借酒裝瘋,恃著那人對他的縱容忍耐為所欲為,他不知道一旦被那人知道他從來都是千杯不醉的事實,這種不知該如何命名的關係會不會就此終結。
他嘆了口氣,伸手拂開那伏在額際的碎髮,墨黑色的眉下有一雙緊閉著的眼睛,先前因體溫驟升而泛紅的臉頰此刻褪了色,有些瘦削的微陷,像是經歷了不知多少年的滄桑。
「從小你就是這樣,明明那人對你一點感覺都沒有,你還是要一頭栽下去。我要是少一點同情心的,根本就不會理你這種白痴。」
他低聲責備,眼見在睡夢中的藍琰彷彿皺了一下眉,他放輕動作,將那頭顱攬在自己肩窩上。
「我還沒有看過像你一樣喜歡折磨自己的人……姓藍的,你看上去明明很聰明,怎知你原來是個不折不扣的傻子……」
但是,在傻子的背後,仍有另一個傻子重蹈覆轍。
他忍不住笑,傻子跟傻子,這配搭不是很完美嗎?
八年前,他在酒吧的洗手間內,無法停歇地將手中的清水往臉上潑,令因酒氣而微熱的臉迅速冷卻。
他還以為自己有的是機會去爭取自己心中的那個人,怎知到了最後,耐心等待的結果是被人捷足先登。
中午的景象,初時令他愕然至極,待他向班中一個不算是深交的女同學探問,她先是一楞,然後笑了:
「他們這樣已經有好一段日子了,你不知道嗎?當初我看到朱見燊餵胡維慵吃藥的時候還覺得有點彆扭的,可現在看得慣了,又知道胡維慵近來身體不好,就覺得其實他們對對方都挺溫柔的呀。」
已經有好一段日子……而他竟然完全沒有發現他們的異樣……
他看著鏡中滿臉水漬的自己,額邊的頭髮滲出了水滴進自己的左眼,那澀意讓他睜不開眼睛,他感到眼眶突地湧上溫熱的感覺,使他在澀痛的不適感消退以後仍不敢張開雙眼。
有人推門走進來,他沒有理會那鞋子摩擦過地面的聲音,直至一隻手覆上他的肩頭。
「阿琰,你別這樣。」
他閉著眼睛,額際隱隱泛起的痛楚使他緊皺起眉,他雙手抵在洗手台旁邊,突然苦澀扯出一笑。
「我不這樣,還能怎樣?難道我應該為這件事向阿燊報復?我又憑什麼去報復他?他們都是我朋友,我怎下得了手拆散他們?」
那人不語,從抹手紙箱中抽起一張,擦拭著他沾上了水的短髮。他緩緩張開眼,看著鏡中人的舉動,不自覺地開始發呆。
那人察覺到他的目光,停下擦頭髮的動作回視他,「怎麼了?」
他像是被驚醒一般猛然搖頭,拉下了那人的手,從他身旁繞過去想走出洗手間。
他知道自己的意識開始混亂,再喝醉一點或者就會不省人事,但這樣比想起那件事來得更好。
那人追了上來,一手拉住了他,「阿琰,你今晚已經喝了很多,再喝下去真的會醉的。」
「我就是要醉,你別管這麼多!」他甩開那人的手,逕自拉開洗手間的門:「醉了以後什麼都不記得,這樣多好!起碼比現在好!」
洗手間外充斥了轟隆隆的電子音樂,他卻能清楚聽見在身後傳來的嘆息:
「這樣逃避現實,有用嗎?」
下一刻他被強硬地拖著出了酒吧,他覺得腦子一片亂烘烘的,也不知道自己將會被帶到哪個地方,只是感覺到自己脫離了那個快要將耳膜震穿的地下酒吧,來到另一個只有微弱燈光的安靜環境,兩地中間像是相隔了很遠但又像只隔著一條馬路,走過的混凝土被徹底清除遺忘。
他就似是被放在一張狹隘的床上,那床讓他四肢被限制著無法伸展,他翻了個身,有一瞬間身體像被騰空,後來卻又像撞到了什麼堅硬的東西一般,背脊隱隱作痛。
有人把他扶起,他卻不知怎地不想站起來,任那人怎麼拉也拉不動他。他用力抽回自己的手,那人遲疑了一下,然後伸臂要把他從那個地方拖抱開來。
「你在搞啥……」他不滿地掙扎,稍一轉首,臉貼上了那人的鼻尖,微弱的暖息拂過他的臉,使他腦子驀地有那麼一刻,清醒地知道自己身在何方,以及,那個不斷將自己拉起來的人。
後來他卻什麼也想不起,不知是誰先做了下一步動作,待他再回復意識,他發現自己將那人壓在地上親吻,那人一手緊箝著他頭顱,另一手解開他白裇衫的鈕扣。他努力退開來,雙手撐在那人的脖子旁邊,勉力睜大眼睛看著身下的人。
「燁,你知道……自己在做什麼嗎?」
那人躺在地上回視他,端正的臉既嚴肅又認真,「知道。」
他聞言苦笑一下,「我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待我明天醒來的時候,你再告訴我吧。」
那人沒有回答他,坐了起來,雙手捧住他的臉繼續方才被打斷的舉動。
後來發生的事,沒有人要阻止,他在翌日張開雙眼,瞧見旁邊一張熟悉的臉的時候,他有些怔然,更多的,是不得不默許自己此等行為的悵惘。
這樣不論對阿燊、阿慵,還是對他自己,都是最理想的做法。
至於阿燁,他已經想好了,將來要盡力為他尋找一個心儀對象,或者待他接手家族生意的時候,盡量為他找機會大賺一筆……
這種荒唐無稽的補償方案,究竟是在補償阿燁還是在撫平自己的罪惡感,他無以回答。事實上,這個念頭想了八年,卻一直沒法實行。
當一切事物不如預料中的進行,便必須再思考出另一個計劃來應付實際需要。
原先的所有草案和念頭,統統將會成為空想。
訂閱:
發佈留言 (Atom)
Link List
Labels
- 記事/廢言 (58)
- 【校園同人】憑劵入場Serial no.U00001(關燁 X 藍琰) (17)
- 【校園同人】蹉跎(袁奉孝 X 郭浩) (16)
- 短文 (16)
- 【校園同人】都說了我不是同性戀(張班長 X 洪無丹) (11)
- 還(荊軻 X 姬丹) (8)
- 【校園同人】做人不要太變態(鍾俊彥 X 何家輝) (6)
- 甕中捉鱉(囊瓦 X 姬申) (6)
- 販售資訊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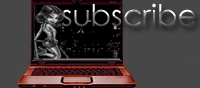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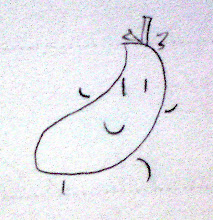


0 留言:
發佈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