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至他聽聞了荊卿與樊將軍會面,心中一陣不祥感驟然湧上,他匆匆策馬出宮,奔至樊將軍舍前,無法顧及自己騎術不濟,急著下馬的動作使他幾乎摔倒在地上。
嬴政揚首要以千金換樊將軍人頭,而荊卿先前亦道,入秦首要之事,即要取嬴政之信任……
奉上大燕地圖,還不足以取信於嬴政嗎?若非得要如此殃及無辜,才可使嬴政人頭落地,這個仇,他還不如不報。
可,樊將軍無辜,荊卿又何嘗不是?
他倏地抬首,淚霧中有著自他入舍以來眉心始終未有舒展的臉龐,那近來一直纏繞他的念頭蓋過仇恨,他不禁慌張,若荊卿發現他有如此想法,不知會有何反應。
荊卿重諾,亦不會輕易許諾,先前荊卿向他明言,將為他手刃嬴政,又豈會反悔。
只有他自己才會反悔,但他無法容許。
自己的轉變被發現得太晚,事後所作的舉動無法補救,唯有順勢而走,同時,在順流中嘗試抽離。
他覺得自己是被一種力量扯離,原本應該一直停留守候的位置離他愈來愈遠,回首之時,尋不回那個地方。
再一次到荊卿舍中作客,這次沒有高漸離沒有歌聲,燭臺乾涸眼淚倒映著秋夜圓月,他沉默舉角而飲,喉頭一如既往暖熱,唇角卻再也無力揚起。
荊卿在席間斟酒,從舍門為他而開那刻,彷彿二人都已無話可說,微冷空氣中間或響起一兩聲秋蟬嘶鳴。
燭火不知何時驀地被黑暗吞沒,他站了起來,摸索著走到荊卿案前,瞇起眼睛在室內尋找微弱月光,這時木案一聲擱下銅角的輕響,而後是一倏然直立在他面前的人影。
他不由自主後退一步,視力彷如突然銳利起來,那因佳釀而微紅的臉,納進他眼底。
「荊卿,」他開口,嗓音在他不為意之下變得比平時粗嗄,「你醉了。」
黑瞳盯著他,不似酒酣的失焦,剛落的話音倒像是他在自我安慰,只有醉酒的荊卿,才會有如此眼神。
耳廓無聲湧上嫣然血色。
「荊卿,你醉了,還是回房歇著吧。」
他匆匆別開目光,走到荊卿身旁,雙手甚至開始攙扶著他返回房內。荊卿默然任他扶著,雖一語不發,他卻仍然感到那眼眸如被人架起的炭火,隨著時間一點一點升溫。
他讓荊卿坐在窗下的軟榻,起身正欲離開,左手手腕驀然被箝緊,悶鈍的疼痛自腕間泛開。
「荊卿?」
他回首,微皺起眉輕喚一聲,紙窗糊散的光暈打在荊卿臉上,眼前瞬即只剩下發白的窗,以及那看不見上頭花鳥紋飾的窗框。
額上起了暖融的感覺,停留只短短一刻即撤離,餘溫從那片肌膚擴散至微悸的心臟,燻得他幾要感到刺痛。
那是鴻毛燎於炭火的疼,雖是戳刺著他的神經,可他為著這難得的溫度,甘願棄卻那足以保他萬全的寒冷。
縱然是當最後化為烏有的鴻毛又何妨,然而他必須用盡全身力氣,以制止自己手臂孟浪環抱面前的人。
「荊卿,你醉了。」
他閉著眼,低聲說出第三句同樣的話,努力把自己從深淵扯出的頃刻,一呼一吸皆是窒息的痛。
一雙手繞過他鵝黃的衣衫,些微急促的呼息間,他聽見荊卿如此說。
「你究竟……在逃避什麼?」
他難以成言,他在逃避的,正是他必須要逃避的東西。
不知是幸或是不幸,自他婉言催促,荊卿怒而拂袖以後,他知道,自己已無反悔的機會,而且,大仇將得報。
卻非在他親自手刃嬴政的情況下。
荊卿不欲再停留於薊,他本為此鬆一口氣,只為自己能及時離開那溫暖的源頭,不至於為此壞了多年的復仇計劃。
寒風捲進他素白衣袖,筑音之中,曾經給予他體溫的人登上車輿,不復回首。
「荊卿。」
他不知為何輕喊一聲,眼眶中似有淚意,出口的兩字迅即崩裂於颯涼空氣之中。
日已盡矣,日已盡矣。
能使他毫無牽掛,一心入秦復仇的時機,早在荊卿為他披上大衣的那刻,悄然而過。
斷絕令自己反悔的可能,並不能同時斷絕,那在他看著溫車漸遠時宛若被奪去一切的感覺,故意使荊卿認為自己只為報一己之仇,無法在同時扼殺,心臟裏頭欲開口阻止他入秦的渴望。
逃出幾要溺斃其中的急湍,在蕭瑟河岸徘徊追尋,踏遍無數野草蒲蘆,始知自己,早已一去不還。
----------------------------------------
下篇應該應該應該是政兒和某人的H><||||||其實這本來是特意寫給我親愛的左貓同學的XD因為她曾經說過「他是看不見的,快推倒他啊!!」的感覺好萌XDDDD
……
……那個某人已經穿幫了不是嗎-_______-|||||
訂閱:
發佈留言 (Atom)
Link List
Labels
- 記事/廢言 (58)
- 【校園同人】憑劵入場Serial no.U00001(關燁 X 藍琰) (17)
- 【校園同人】蹉跎(袁奉孝 X 郭浩) (16)
- 短文 (16)
- 【校園同人】都說了我不是同性戀(張班長 X 洪無丹) (11)
- 還(荊軻 X 姬丹) (8)
- 【校園同人】做人不要太變態(鍾俊彥 X 何家輝) (6)
- 甕中捉鱉(囊瓦 X 姬申) (6)
- 販售資訊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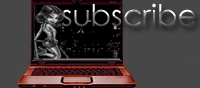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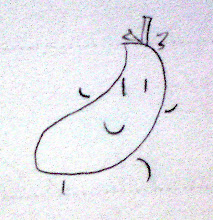


0 留言:
發佈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