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戌時,姬申依約來到囊府廳外,尾隨的四名家僕靜站在他身後,面無表情地盯著他斂眉,沉默地在廳門前佇立,似在等待。
淺棕髮冠罩住了他墨黑的髮髻,額際光潔,是尋不到半縷碎髮的一絲不苟。白玉般的臉龐上沒有表情,僅只淡粉的淺抿的薄唇,透露了他暗藏於心的忐忑。
門上嵌著糊了紙的窗,窗中泛著白,在夜色下顯得有點刺目。姬申面對著大門,身上一襲鵝黃的深衣沉浸在昏暗中,已然看不出原來的顏色。
在門外,他一直在等,直至半個時辰以後,大門被廳內之人打開。
「原來蔡侯早已來到了。」
囊瓦挑起一眉,話語中全無怠慢國君應有的理虧,黑瞳更是毫不客氣地打量了立在門外的身影一番。
此等裝扮下,這蔡侯看來並非瘦弱之人,但上回他出手箝制他,只消一掌,便可以包覆住那隻手腕,輕易便能使他動彈不得。
身體孱弱得有點……出乎他意料之外。
在他印象中,國君應是勤練劍技射術,不然也是經常駕車到城郊打獵,身子理應頗為強壯才對。
「蔡侯或許不知道,在下剛才只是虛掩廳門,蔡侯大可推門而入。」囊瓦收回視線,露出一抹近乎嘲弄的笑意,側身讓路予姬申。
姬申得知自己被愚弄了,清秀的臉頓時扭曲了一下,立刻便恢復成淡然的模樣,不冷不熱地回道:
「寡人自小禮教甚嚴,不會未經廳中人允許便擅自入內。難道令尊並無要求令尹嚴循禮儀,以致令尹不知有此規矩?」
本來就是在故意讓他在外等好一陣子的囊瓦,聞言也無慍怒之色,「回蔡侯,家父管教尚算嚴格,但在下實在不覺得,有必要禮待一名囚客。」
囚客?
姬申聽到這侮辱性的稱謂,怒火霎時炸上他的腦門,他上前,兇狠的目光死瞪著囊瓦,話語自齒縫間一字一字屏出來:
「寡人既是囚客,也無需再對令尹如此多禮。」
話音剛落,他掄起拳頭,想也不想地一拳揮去。
囊瓦避開了直朝面門而來的拳頭,大手一抓,迅即捏住了不盈一握的雙腕,俊臉湊上去,眼對眼,鼻對鼻,揚著唇說:
「話說回來,蔡侯實在應好好感謝在下一番。」
盛怒之中,猝不及防,被迫正正看著那雙黑眸,眼瞳中的倒影,清澈得讓他不禁怔然。
氣息噴吐,輕拂在臉上,平日難得感覺到的微溫。
不曾與人如此接近,這種觸感很陌生,陌生得令他心悸。
「寡人為何要感謝你?」
暖息間,他啟唇輕吐,語氣驟冷。
「若非在下,恐怕蔡侯不會有動武的機會。」
囊瓦微笑著,在他唇前喃道,雙手被他制住的國君,沒有多餘的掙扎,只是冷冷回視他。
掌間有著細膩的觸感,他不否認,他愈來愈喜愛這種使人心情舒暢的感覺。
「蔡侯似乎不善於動武,身體也不甚強壯。」
蔡侯實在很瘦,瘦得讓人,忍不住想狠狠蹂躪他一頓,加上他那張臉,簡直就是在考驗他的定力。
從一開始,看到了這個人,他就已經如此想著。
「因為寡人從來都無動武的必要。請令尹放手。」
姬申勉力掩蓋心中的那股奇怪的感覺,語氣仍然冷得似結了冰。
意外地,囊瓦立刻放開了他,轉身踱至廳中另一端,慢條斯理地坐下。
「蔡侯請坐,以方便下人傳膳入廳。」
姬申這才注意到自己一直站在廳門前,僵著臉走向廳側,跪坐而下,冷眼看著下人捧著一盆盆冒著煙的菜餚,魚貫地膝行進廳。
米飯、熱湯、烤魚、燴菜,一盆一盆端上,姬申拿起案旁的角,仰首淺淺啜飲味道尚算不錯的甜酒。
這令尹,看來仍然尊重他這名國君,起碼在膳食上,他所受的待遇還算不俗。
忍不住斜目瞥去,俯首進食的身影彷彿毫無所覺,薄唇微張,納進銀箸上的一小團米飯。
腹鳴驀地傳來,姬申尷尬得臉一紅,匆匆放下酒角,執箸一口接一口地開始進食。
廳中靜謐得足以令人錯愕,兩人剛才明明幾乎要大打出手,此時卻能安靜地同坐廳內用膳。
或許連他自己都不想再多作無謂的爭執,反正就算他如何破口大罵,這令尹也不會肯輕易放他回行館,然後離楚回蔡。
只是他不放心,大蔡本已非強國,若他國趁大蔡國內無主之時派兵討伐,恐怕即使有兄長坐鎮,也無法擊退敵軍。反之,若他在國內,大蔡軍力雖不會有所增減,但或多或少能鼓舞將兵士氣,甚至對外虛張聲勢。
國不可一日無主。
不如……索性去信大蔡,要求兄長重登國君之位?
不行,不行。兄長當初堅持詐死讓位,他不能破兄長之謀……可他這國君被囚之事非同小可,此消息理應傳遍了中原各國,若向外散佈他已回國的消息,天下人也未必相信。
「蔡侯停箸,是因菜餚不合口味嗎?」
姬申回神,側首瞧見囊瓦一手握著酒角,一手托腮,正揚眉盯著他。
「令尹誤會了。」他回道,垂眸繼續進食的動作,可那兩道秀氣的眉毛,悄然往眉心靠攏。
對自己無法回國,他痛恨又無奈。
他明明是個國君,卻受制於人,這蔡侯,做來還有何意思?
「蔡侯,若菜餚不合口味,請別勉強進膳。」囊瓦眼尖地盯著他眉心淺淺的皺摺,語氣淡漠。
他向來都不打算在膳食上虧待蔡侯,若果能以此籠絡他,讓他交出珮裘,那當然非常不錯,雖然他清楚這絕不可能會發生。
可是,看著他進膳時皺著一張臉的模樣,他竟覺得有種……心機被糟蹋的不快感。
「貴府膳食非常合寡人口味,只是寡人……」姬申吞嚥下鮮美的魚肉,開口辯駁,待說話吐出唇間,他方驚覺,自己根本不用如此急切要向這令尹解釋。「寡人正思考一些……急需解決的難題。」
那個所謂難題,應與蔡國有關。囊瓦不動聲色,捧角就唇,嚥下泛著香氣的佳釀。
「……令尹。」姬申擱下銀箸,低垂的臉龐久久沒有抬起,「寡人有事相求。」
囊瓦一臉興味的繞高了俊眉,凝視那張臉蛋已然有些泛白,不禁淺揚起唇角。「蔡侯請說。」
姬申閉目深深吐納,良久才艱難地挪動身子,膝行著來到囊瓦案前,對視他狹長的雙目,咬了一下唇,低聲說。
「求令尹放行,讓寡人回蔡國。」
語調生硬,他忍著心中強烈的恥辱感,頭垂得比任何時候都更低,白淨的頰邊,不知何時浮上淡淡的羞愧紅暈,取代了先前的蒼白。
囊瓦起身走至他前面,施施然坐下,伸出一手輕托起他下頷,詳端他微紅的臉,遲遲不發一言。
這一侮辱至極的動作使姬申恨恨咬著牙關,然而他有事請求在先,只得壓下揮開那隻手的衝動,任由帶著些微粗糙感的指腹輕撫著他下巴。
為了回國,必定要沉住氣,去爭取那渺茫得令人氣餒的機會。
「在下真的感到非常……受寵若驚。」黑眸輕瞇,眼前乾淨清秀的臉龐聞言瞬即僵了一下,「蔡侯肯如此放下身段,在下也感到很好奇,究竟因何事能令蔡侯主動開口,請求在下放行。」
那隻手依舊在他下頷撫摸,微癢的觸感起初讓他既氣惱又羞恥,可是他除了想閃躲之外……並沒有任何強烈厭惡的感覺。
如此一個動作,只要不讓他人瞧見,沒什麼大不了的。
姬申在心中說服自己,嘴唇抿了抿,聲調並無起伏,「國不可一日無主,令尹想必也明白此道理,寡人也就無需多作解釋了。」
眼前的人,分明極欲掙脫他的掌控,卻不得不隱忍的模樣,淺淺的緋紅嵌在兩頰,是羞恥和佳釀的甜香抹上的。
囊瓦承認自己向來貪戀美色,然而這張臉,無論如何也稱不上是艷麗,與他往日所喜愛的美人……似乎尚有一段距離。
怦怦,怦怦,清秀的五官乾淨,沒有抹上脂粉,單單臉上兩道淡紅。
顫動的心房深處,隱隱竄起了一股想要掌握什麼般的強烈渴望,他漠然以對,那只是自己一時錯覺而已。
「蔡侯為何如此肯定……在下可以放你歸國?」囊瓦露出平靜的微笑。
「……」姬申一時語塞,抬眼瞪向他,面色紅了又白,白了又青,青了又紅,顯然為自己的辭窮尷尬不已。
他找不到證據指控這令尹,說是他向楚王搬弄是非,使他不得返蔡。
「令尹……權傾楚地,就只有你能勸說楚王。」
囊瓦笑意加深,俊臉湊近,壓低了聲音喃道,「蔡侯,容在下問你一句,在下替你說服大王,對在下有何好處?」
姬申突然感到有些呼吸困難。
不是因為他的話,而是因為那張臉,帶來了太大的壓迫感,在近距離下看去,眉眼如星,輕而易舉地惹得他怔忡不已。
若非他令人反感的言行,這令尹的確是個引人注目的貌美之人,回想蔡宮中,竟是無一人能與之相比。
姬申嚥了嚥口水,艱難地啟唇:「令尹何不想想,貴國與我大蔡乃兄弟之邦,若令尹肯幫助寡人回國,日後貴國若有需要,大蔡定必不辭所托。」
話語間,唇瓣一次又一次,輕熨過正漾著笑的薄唇,姬申一邊說著,一邊不由自主地把臉漲得通紅。
下頷仍在面前之人的指掌間,只要他稍一退避,就會使這令尹得到拒絕他請求的藉口。
囊瓦壓下心頭激越,微笑不變,指出了事實,「蔡侯提出的所謂好處,非在下能享之好處。若蔡侯今日所請求之人是大王,依照蔡侯剛才提及之利,大王說不定會答允蔡侯所求。」
難以避免,因那細軟觸感而起的身體反應,然他很清楚,他要的,絕不是一時的短暫擁有權。
原來不是錯覺。
一珮,一裘,一人。
三樣物件,一樣也絕不能少。
有生以來首次低聲下氣的請求,被拒絕了。
姬申緊捏著刻刀,一片竹簡橫躺案上,嵌滿了深淺刻痕,他咬牙,狠狠在簡上劃了好一會。
有想過把房中一切擺設都毀壞殆盡,可他知道,那令尹不會因他這種遷怒的行為而放他回國,若是如此,他倒不如省一點力氣。
「啪」的一聲巨響令木案震了震,姬申瞠著雙目,死死瞪著在他刻刀下硬生生折斷成兩半的竹簡。
他不可在此地多作逗留,即使無法得到這令尹的同意,他也一定要回到行館,而且盡快返蔡。
不過……房外日夜駐守的四名家僕,該如何做才能把他們支開?
修長白晢的指尖輕敲木案,窗戶上從刺目的白染了些許淡黃,姬申站起來,苦思良久仍想不出一道計策來。
前所未有的氣餒。
噹啷,淺藍的衣袖一揮,平空劃了個優美的線弧,一柄小巧的刻刀自袖間飛出,墮地。
與此同時,房門傳來一陣輕響,姬申皺了一下眉,冷著嗓音揚聲問:
「來者何人?」
敲門之人擁有一把嬌柔好聽的嗓音,使姬申有點不在意料之中。「回蔡侯,妾奉令尹之命,送來溫酒讓蔡侯服用。」
「……」他實在不明白,數天前晚膳之時,那令尹猶在羞辱他,說他是一名囚客……
然而,回想在他被囚囊府後的種種,他不得不承認,他所受的待遇,不能說是差劣。
這令尹,必定懷有某種目的才會如此禮待他,說不定是想藉此籠絡他,好讓他心甘情願奉上那一珮一裘。
奉上珮裘,不止失了寶物,更有失身為國君該有的臉面。堂堂蔡侯,居然受制於一名楚國令尹,情以何堪?
絕對會有一些封國因此了解大蔡外強中乾,派兵來擾……雖然,他大蔡實非中原強國,而他本身,亦無稱霸中原的野心。
反正他這名蔡侯,只是被兄長硬推上去當的。
門外人不聞他有拒絕之意,便推開房門,雙手捧著一盤,小心地抬履跨進了廂房,纖細的身影移到木案旁邊,輕巧將盤上一爵冒著熱氣的酒漿擱下。
是那位女子,囊令尹之妾。
黑瞳盯向熟悉的嬌艷面容,若非她手捧托盤,姬申幾乎以為,曾經看著他讀書習字的臉龐,此刻又回到了他身旁,微笑看著他。
女子放下盤上銀觚,垂著頭站在原地,驀然開口。
「蔡侯,妾……妾奉令尹之命,照料蔡侯起居。」
「寡人知道。」姬申伸手想捧起銅爵,指尖才剛觸到爵緣,便立刻被燙得縮回了手,皺起眉朝微紅的指尖吹著氣。
「蔡侯小心,此爵方溫好酒,若蔡侯欲飲,妾這就為蔡侯斟酒。」女子說著便伸手欲拿起酒爵,姬申忙不迭按住她。
「算了,寡人不急於飲酒,可待此爵稍涼時再行斟酒。」姬申忍著手指上遲遲不散的灼痛,故作輕描淡寫地問:「妳叫什麼名字?」
「回蔡侯,妾自小無名,得令尹收留,才能有幸服侍蔡侯與令尹。」女子垂睫,雙手扭絞著衣袖,低低回答。
姬申閉上眼睛,那面容讓他想起一抹身影,在枯黃落葉間旋舞,翩飛的橙黃衣袖,幾可與周遭融為一體。
他那時仰首,雙眼輕瞇著抵抗微冷的風,在這天氣,穿著黃綢的姊姊難得沒有督促他回宮練字。
風蕭葉落。
「若妳無名,寡人喚妳時豈不會很麻煩?」姬申睜眸,原本冷漠的目光放柔,看著始終不敢抬起來的秀容,「寡人為妳取個名好了。」
就不知,身為這女子的夫君的囊令尹,會否因此介懷。
長著與姊姊一模一樣的臉,卻無半點姊姊強悍的氣焰,當然,也不會膽敢扠著腰立在他身旁,監視著他讀書。
姬申漾出一抹懷念的笑意。
「蕭兒,令尹如何吩咐妳侍奉寡人?他可有命妳貼身跟隨寡人?」
雖然此女並非他親姊,不會監督著他每日作息,可若那令尹要她貼身跟隨他,他能逃出囊府的機會更是渺茫。
女子忙朝著姬申跪下,「謝蔡侯賜名之恩……令尹並無吩咐妾貼身跟隨蔡侯。」
她抬眼,黑白分明的清澈杏眸觸上另一雙黑瞳,隨即受驚似的挪開視線。「……只是……」
「只是?」姬申疑惑地瞧著她垂下頭,兩頰紅得似要滴出血來。
「……」她咬著花瓣般的唇,支吾了半晌,才說道:「……若蔡侯無其他吩咐,請蔡侯容妾先行告退。」
有古怪。
到底是什麼,能令這女子如此難以啟齒?
那句「只是」的下文絕不單純,或許是那個令尹透過此女欲對他作出一些無理要求,又或者,是命令此女作出一些使人尷尬不已的事。
蕭兒那沒有說出的下文,完全勾起了他的好奇心。
然而他明白,縱然他強迫這女子說出下文,也未必能套出實情,而且,他如今首要做之事,是逃出囊府。
因此,別再多作無謂的猜測了。
「妳先下去吧。」姬申放棄追尋真相,擺了擺手,蕭兒捧著空無一物的托盤,彎腰退出廂房。
有些頹然,姬申怔怔瞧著房中一角擺放著的書簡,姊姊以往嚴令他背誦起來的禮書兵籍,到了這個關乎大蔡存亡的時候,全然失去作用。
國中無君,局勢不穩,變亂難定。
指尖輕輕碰觸銅爵,確定它不再滾燙,姬申沒有將爵中酒液倒進銀觚,而是直接舉高,把佳釀都倒進了口中。
入口的酒仍然有些燙,他口腔一陣輕微的痛楚,待適應了瓊漿的溫度,唇舌間才嚐到了淺淺的澀意。
美酒獨有的醇香襲進鼻間。
姬申把爵中酒飲盡,隨意把銅爵一擱,蹣跚地朝床榻而去。往常他所飲的盡非楚酒,剛才的楚酒,與他以前所飲之酒相比,更有一種說不上來的獨特之處。
這令尹是故意的,明知道他非嚐楚酒之人,為了防止他逃走,特意送來了這爵酒,使他連這間廂房也逃不出去。
姬申皺眉躺上床榻,伸手拉高了被衾。
可是,現在的他,不想再繼續苦思逃走的方法。
這還得多謝囊令尹,適時派了人,送來了這麼一爵酒。
----------------------------------------
......這文寫到後來其實連自己也覺得很囧= =希望看倌們不要介意這文中扭曲了的攻受人格(鞠躬)
訂閱:
發佈留言 (Atom)
Link List
Labels
- 記事/廢言 (58)
- 【校園同人】憑劵入場Serial no.U00001(關燁 X 藍琰) (17)
- 【校園同人】蹉跎(袁奉孝 X 郭浩) (16)
- 短文 (16)
- 【校園同人】都說了我不是同性戀(張班長 X 洪無丹) (11)
- 還(荊軻 X 姬丹) (8)
- 【校園同人】做人不要太變態(鍾俊彥 X 何家輝) (6)
- 甕中捉鱉(囊瓦 X 姬申) (6)
- 販售資訊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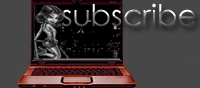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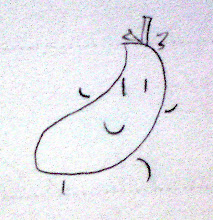


0 留言:
發佈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