嬴政立刻醒了過來,一手捂著被打中的鼻一手撐起上身,他迅即穿履下榻,忍著不適感自宮中角落找來乾淨衣袍,抖開了便匆匆著上。
「丹兒。」
嬴政猶在榻上喚道,那聲音因為摀住鼻子而含糊不清。他不理會,翻開箱子找出自己所有衣物刀幣,將一切都放在布袱之中,繼而挽著袱站起,走過床榻之時,衣襬冷不防被拉住。
他不看那人一眼,只用力掙開那隻手,步上前使勁推開宮門,雙足跨出門檻之時,宮外猛烈光線讓他眼前昏盲片刻。
他曾是如此相信榻上此人,最終這信任,由那人親自毀滅。
國小被人欺,他從來都能明白這一點,但即便大燕非中原大國,他仍為太子,此種待遇,他無論如何也不能就此罷休。
若非他手中無劍,嬴政早已氣絕榻上。
他本欲以劍自裁,卻被人阻止,如今他已無自盡之念頭,因為,在他赴死之前,必先使嬴政命喪於他手中。
他要回到薊都,帶著破碎的尊嚴回到那有著父王母后的地方,只有如此,方能拾回他應得的一切。
輾轉五年,他所尋者,無一肯助他一臂,以解大燕之國危。不論當中多少賢者豪士,在聽聞他早已策劃之計後,皆不苟同地勸他勿行此策。
只有田先生在得悉他的盤算後,謂要引一名勇士來見,他看著那佈滿皺紋的臉,忍不住道了一句。
「今日與先生商討之事關乎大燕存亡,還望先生勿泄。」
雖然明白田先生乃言而有信、足以托付大事之賢人,非嬴政之流可與之相比,但他還是不放心。
他僅相信自己,在被唯一相信過的人欺侮過後,令他無法再給予任何人十足的信任,因為無人能確保誰會在下一刻換上另一張臉孔,就如那嬴政一般。
然而他最終只能向著由田先生薦來的荊卿連連叩首,如何也料不到自己一句話,足以置人於死地,欲追悔時已鑄成大錯,眼淚再流也不能使人起死回生。
荊卿一直沉默著聆聽他的說話,那些話語連自己都覺得像是在自辯,事後回想,也不禁失笑。
難怪荊卿當時一語不發。
「敢問太子殿下……微臣應當如何,方能鏟除秦王?」
直至言及國家大事,荊卿才開口問道,那聲音比他想像中更為低沉,微帶沙啞卻與他略低的嗓音協調非常,他心中好奇,低首以袖拭去因眼淚而模糊的視野。
那面容嚴肅不帶笑意,雙眼深邃,讓人難以想像他失儀縱笑的模樣,相貌非特別出色,但他覺得甚是順眼好看,唇很薄,薄得只瞧見兩條淺紅的線,彷如在抿嘴唇一般。
他向荊卿述說著那已思量五年之計劃,瞄向案上的地圖,不期然發現,報仇之念已在心中蘊釀多年,今既有人將為他一雪此恨,然而今後一旦殺了嬴政,他還有何目標迫令自己苟活於世?
身為燕太子,卻自小質於國外,近年方得以回薊,早已過了一名太子為學之期。他不曾習武,不詣大燕內政,不知國內穀物何時收成;縱然在太傅教誨下尚算有小成,他所學亦不能輔佐父王,使大燕國勢轉弱為強。
他知道父王最為器重的,乃他的王弟,他這名太子只不過是因父王為防王弟們奪嫡而自相殘殺,才得以在燕宮中保住位置。
他沒有向荊卿道出實情。
入秦之人,非只有荊卿,還有一位除了能平息燕公子間之紛爭外一無是處的太子丹。
有荊卿為舍上客,也許他能向他討教武藝,只要他能略詣劍術,足以供他用於秦庭上。
一雙手托住他的臂膀,使他頓住動作,仰首凝視這唯一未有勸他放棄入秦的人。那雙眼彷彿在找尋他眸中誠摯之色一般,後又默然別開,他看不出埋藏在那眼瞳下的心思,只得以目光緊追不捨。
他是他唯一的希望。
訂閱:
發佈留言 (Atom)
Link List
Labels
- 記事/廢言 (58)
- 【校園同人】憑劵入場Serial no.U00001(關燁 X 藍琰) (17)
- 【校園同人】蹉跎(袁奉孝 X 郭浩) (16)
- 短文 (16)
- 【校園同人】都說了我不是同性戀(張班長 X 洪無丹) (11)
- 還(荊軻 X 姬丹) (8)
- 【校園同人】做人不要太變態(鍾俊彥 X 何家輝) (6)
- 甕中捉鱉(囊瓦 X 姬申) (6)
- 販售資訊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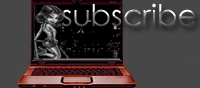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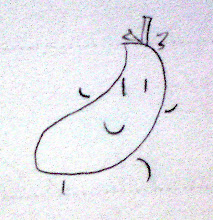


0 留言:
發佈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