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告訴自己,那天晚上之事,不過是因為他子夜仍未離開,而荊卿酒醉,才會盡失其度,又何必耿耿於懷。
他開始每夜留於荊卿舍中,酒後靜靜傾聽荊卿放歌,偶爾荊卿亦會邀高漸離作客,一人擊筑,一人吟唱,每每目睹此種情景,他都覺得,自己是被二人隔絕於外了。
凝睇此種場面,最後自己總是忍不住,默然離開大廳,反正那二人酒酣之中,除了奏樂和歌,對身邊之事一無所知。
他開始向荊卿請教武藝,荊卿自得悉他並無練武根基後,便授他一些簡單的拳腳功夫,以及自衛之術。
他明知無法一蹴而就,但也不願拖延時日,只得在宮中勤加練習,結果卻使他翌日全身酸痛得幾要動彈不得。
「殿下根基不穩,何苦如此急於練武?」
荊卿邊攙扶著他往舍內走,邊將兩眉皺緊,他苦笑一下,「若我再不加緊習武,只怕往後再也來不及。」
「敢問殿下何出此言?」荊卿停下了腳步,俯首與他對視:「誠如殿下先前所言,只要臣入秦能順利脅迫秦王退還大燕之地,大燕便可得以扭轉敗勢。而殿下亦暫無後顧之憂,到時候再行習武也不遲。」
他笑笑搖首,荊卿到此時仍未清楚他全盤計劃,而他,明明托荊卿之助以雪前恥,怎麼能繼續向他隱瞞。
「實不相瞞,先前我曾向荊卿道過的刺秦之計,有某部份……我本並不打算讓荊卿知情。」
荊卿瞠目的模樣令他不禁莞爾,他不著痕跡地掙開荊卿的手,負手踱了開去,淡然啟唇。
「若不親自手刃仇人,又豈稱得上復仇?」
「殿下!」
身後傳來的嗓音嚴厲得使他一怔,輕皺起眉回首,卻見荊卿走上前,微抿的唇似是慍怒。
「殿下乃大燕之儲,豈可入秦涉險?微臣懇請殿下打消此念。」
他默然凝睇,垂眸回視他的臉龐比往日更肅穆,然而他卻能依稀辨出,那眼中並非惱怒。
不知何時,嘴唇沉重得再也無法牽起笑意。
「荊卿,自我亡歸燕,五年以來,無一日不想起此仇仍未得報。」他別開臉,揚首望向頂上深棕橫樑,說到最後不禁苦澀一扯唇角。「殺嬴政乃我唯一心願,還望荊卿勿使我要抱憾此生。」
荊卿不語半晌,他朝他一彎唇,旋身正要步至廳中,忽爾聽見身後一聲悶響,令他忍不住回首。
眉心無法抑止緊緊斂起,他走到低首下跪的身影面前,伸手欲將他扶起,「荊卿,你這是何為?」
跪在他跟前的人動也不動,僅抬起頭,道出的話語決絕,全然不似請求。
「請殿下允許微臣替代殿下,入秦手刃秦王,以報殿下之仇。」
他厲目而視,心中竄上的悲涼無法忽視,數天以前,肩上厚衣與一雙同樣厚實的手,渡進了一絲微暖的感覺,他笑了,有些微靦,更多是為心中一閃而過的念頭。
若果能一直這樣,也不錯。
可是他又同時很清楚,從一開始,他就截斷了自己一切去路,不讓那糾纏了自己五年的仇恨最後得不到解決。
他早已明白,不是嬴政死,便是他亡,才能了結此仇,而嬴政一死,他也絕不可能逃避得了秦廷上為嬴政復仇的劍刃。
既然知道自己從來無活路可走,為何還要出此謬誤?
全然不能控制,對那人那掌心暖意的貪戀,打亂了他全盤報復計劃,彷如久處嚴寒之下偶見炭火,便忍不住要伸手觸碰。
也許是因為近來與荊卿相處太久,方會生出如此錯誤的念頭。
自此他刻意疏遠荊卿,非有必要也不到他舍中作客,他需要回到自己那始終寒冷如冬的王宮中,只因一旦對炭火養成了依賴眷戀的感覺,即使火焰燙傷了手也會無法再受忍那無一點溫度的冰冷。
訂閱:
發佈留言 (Atom)
Link List
Labels
- 記事/廢言 (58)
- 【校園同人】憑劵入場Serial no.U00001(關燁 X 藍琰) (17)
- 【校園同人】蹉跎(袁奉孝 X 郭浩) (16)
- 短文 (16)
- 【校園同人】都說了我不是同性戀(張班長 X 洪無丹) (11)
- 還(荊軻 X 姬丹) (8)
- 【校園同人】做人不要太變態(鍾俊彥 X 何家輝) (6)
- 甕中捉鱉(囊瓦 X 姬申) (6)
- 販售資訊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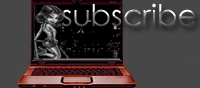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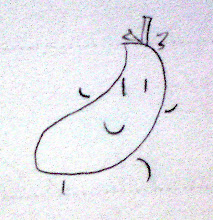


0 留言:
發佈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