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入鐘室,未有那立體分明的面容,只見一旁那相對了數十年、早已失去所有感覺的臉龐,他兩手猛地冒出一層薄汗,密密地,覆住粗糙手掌心。
「他死前,可有留下隻字半語?」
那臉龐徐緩靠近,木然不帶表情,他想起自己當初曾在沛縣感受過的溫婉體貼,可那曾給予他的感覺,猶如木匣上覆蓋了塵土,以手撫摸匣面,也無法憶起匣上雕紋的形狀。
「他說,他後悔自己愚蠢,未有納蒯通之言。」
他頰上細紋抽搐,他認得那是一位辯士,當年那辯士慫恿著他的齊王離他而去,鼎足而立,與他、與楚軍逐鹿於中原,他不動聲色地聽著探子回報著來自齊地的消息,牙齒難以自己地咬緊,他的齊王會否接納那辯士之見,他無法肯定,跳動的內臟時而重重敲著耳門,時而榨出他一手冷汗,將他折騰得於清晨自榻上猛起。
該死的辯士,該死的儒生。
他就知道,他的齊王急於立功,方發兵突襲齊地,攻齊後又強迫他將他封王。他迫於形勢答允,卻無法抑止心中咆吼:
做什麼齊王?在他身旁為他打天下不好嗎?
蕭何帶著他新拜之大將步入軍營那刻,他目光被定在了那臉龐上,鼻樑起伏如經匠工巧手,漆黑眼瞳似初冬雪,在壇案前清冷無痕地擦過,繼而落在他瞳仁裏。
「如今大王若揮軍東進,必可平定三秦。」
那個人開了口,剪開的兩片嘴唇微紅,吐出低柔字句,卻字字皆是洞察之語,他淺笑傾聽,心中隱約明白,這用兵如神的人,就是衡量過思量過當今局勢,方對他俯首稱臣,而他俯首稱臣之目的,不會只是甘願當他手下一員大將。
可他偏偏無法接受,那個人身上有股特殊氣質,在投足舉手微笑凝目之間如野獸揮爪,向他直撲而來,身上血痕讓他恍然,自己根本無以抵抗。
尖長的爪甲拖著他,進入了一個使他難以再全身而退的地方。他暈眩地被拖著前行,鼻尖甫嗅到自己從口中逸出、那屬於新酒的氣味,隨即隱沒於另一股味道之中。
他知道自己以手捏住了那人的下頷,打斷了那個人的話語,舌尖觸碰到熱緣即緊緊纏上,臂膀如繩索將那深詣兵法、為他帶兵征伐過無數次的身軀綑綁,無視那副身軀從掙扎變成了顫慄,慢慢地、慢慢地,竟似融入了那片衣料。
「有人告你謀反。」
他面無表情向他說出了這一句話,那被繩索縛緊的身軀猛然一震,仰首直射向他的目光銳利而清澈,彷彿是新井裏未被微風拂動的、猶如凝固了的冷水。
「所以,陛下相信了此人之言?」那人開口,語氣中的嘲弄令他皺眉:「微臣隨陛下征戰多年,猶不及區區一個不知名姓之人?」
他眼眸不由得停歇在那眉眼之間,那是他最鍾愛的風景,一瞥再瞥也未嘗饜足,只好以君王之名宣告於天下,一切山水秀色,向來皆歸他所有。
他昔日的大將,究竟是不明白這個道理,還是,不想明白。
「朕所做之一切,皆為保我劉氏大權。」
「微臣所做之一切,不也是為了……」削薄的唇欲要衝口而出,卻沒了下文,默默緊抿起來,勾勒出倔強不甘的線條。
車窗透出的微弱光線中,他左掌逐漸靠近那忿然的臉,掌心隔著空氣描繪那臉頰的輪廓,那他喜愛的眉眼瞪得滾圓,看得他有種想發笑的衝動。
「回長安吧,回長安輔佐朕以成大業。」他語調比平日都要軟,他很清楚,天下人眼中孤高自傲的楚王韓信,在他面前向來吃軟不吃硬,最是不能抗拒他這般語氣。
可偏偏,除了此項根本不算弱點的弱點之外,他在他眼中臉上身上的細微動作間,一無所得。
靜謐凝視之間,他看見那濃密的眼睫顫了一下,讓他想起往日,在他仍為小小一名平民之時,他百無聊賴窩於房中榻上,看著一只青蠅落在他臂上,如此輕盈,細細的足點過他肌膚,微癢的感覺無聲無息擴大,他想以指尖壓制,臂膀直至心窩,卻不知如何遏止。
他見過那扇睫毛緊張輕顫,在極近幾要模糊了視線的距離下,彷彿是他熾熱的呼息拂動所致。
他眼眸不由得牢牢定在那兩片嘴唇上。
數年以來,他如何對這一切朝夕渴求,自己最為清楚不過。
微啟唇間露出細白牙齒,他怔忡想起,朦朦朧朧,舌尖掃過牙床的觸感,宛若被百爪撓著心臟,麻麻癢癢。
「……」他看著屬於諸侯王的髮冠一沉,意氣風發的臉龐低眉順目的模樣,卻挑起他一剎不忍。
「臣,遵旨。」
那句臣遵旨,他本以為他是心甘情願的。
流言不知何時開始愈傳愈廣,他這名新帝妒楚王領兵之才,為鏟除一切威脅,以謀反之名將楚王改封為侯,使其不得於楚地策劃反漢。他聽得唇角微揚,繼而向朝他匯報的心腹一勾指,示意他附耳過來。
朕要全天下人都知道,淮陰侯蓄意叛漢,為朕所悉。朕格外開恩,將其貶為侯,然淮陰侯心有不甘,向外揚言當今陛下妒其將才。他笑得眼睛都瞇了起來,彷彿他向心腹所吩咐之任務,只不過是備好新酒,好令他在夜晚能與眾位曾與他一同打天下的老臣暢飲一般簡單。
當流氓當了數十載,也不差在這一次。
那回,他的楚王在車上對他欲言又止的模樣,是他平生首見。楚王韓信的快人快語素為人所稱道,如今這般的應對與表情,究竟是什麼意思。
可他已然無法追溯,自那次之後,楚王默不吭聲接受了淮陰侯之位,默不吭聲窩在京城的侯王府中不出半步。
陳平曾向他進言,應派重兵駐於淮陰侯府以防有人逃回楚地,可他事後卻發現,根本多此一舉。
或許他是想收斂鋒芒,向陛下宣示其忠,陛下萬萬莫要被他這般把戲所蒙蔽。陳平曾道,他只淡淡一笑,未有辯駁。
若他的淮陰侯懂得玩這般把戲,早就有對應之策以免自己被捉拿回京,如今也不會落得如斯田地。他只想不到,縱然淮陰侯早已無實權,朝中仍有視他如威脅之人,甚至要除之而後快。
熟知兵法的淮陰侯,不會不知道這一點,可他遲遲不見他作出任何反擊之舉動,宛若已經不在乎朝野中一切閒言閒語。
微臣隨陛下征戰多年,猶不及區區一個不知名姓之人?
淮陰侯曾這般質問著,他幾乎能從嘲諷的話語下,察出那一絲不知是失望還是痛心的情緒,當日他所得到的反應如此激烈,叫他如何能相信,淮陰侯如今能對那些不利於他的流言無動於衷。
為何他沒有回擊,為何他可以對這一切全不在乎。
他究竟在想什麼。
下令造訪淮陰侯府,看似是一時興起,實際上,他一直都想看望,那個曾官拜大將軍、如今卻如籠中鳥的人,看他日子過得如何,看自己出於私心而下的決定,到底是對還是錯。
府中的家僕魚貫立於門外,低首相迎,目光尋不著那晝夜思及的臉龐,他不禁眉毛一擰:
「淮陰侯不在府中?」
「回陛下,侯爺……侯爺正在飲酒,吩咐小的傳話……」其中一名男僕道,「侯爺不便晉見陛下,還請陛下見諒。」
淮陰侯……好大的架子。
他挑眉冷笑,「朕要見淮陰侯,難道還要得他首肯?」
下一刻他直接推開銅門跨進侯王府,如野豹逐兔一般穿過庭園,在廊間搜索追尋,最終佇立在一房門之前,默然傾聽房中偶爾傳出銅角碰撞木案的聲響,以及,盯著門上照得一團模糊的黑影。
那剪影全無輪廓可言,何處是髮冠,何處是眉梢鼻樑,他都無法看得清楚,可他卻伸出手,徐緩推門而入。
房中所見卻是一抹醉倒案上的身影,一名女子站在案側兀自斟酒,待看見他時,便低首一襝衽:「賤妾參見陛下。侯爺酒醉,不能親迎陛下,望陛下──」
「退下。」
他冷冷開口,那女子一遲疑,迅即識時務地退至門邊,「賤妾告退。」
趴在案邊的人左掌動了動,在案面摸索著,他先一步跨上前,輕巧取走在那指尖側的銅角,仰首一飲而盡,繼而微俯下身,低聲在那泛紅的耳廓旁說道。
「淮陰侯,朕親臨貴府,何不親自出迎,反而在此獨酌?」
他的話語彷彿喚醒了他,只見那案上的臉龐緩緩抬起,昏黃光線折出那雙頰微嫣,清冷孤高消失於半閉的眼眸間,眼黑眼白,僅剩異樣水光,宛若冉冉凝聚於微挑眼角。
「劉季。」
頎長身軀不由得一震,五年十年十二年,他上一回聽到他人如此呼喚這個名字,已然是不知多少個年頭之前的事,他是沛公,是漢王,是大漢皇帝,他這根本不算名字的名字,自他起兵之始,早失去了蹤影。
不論是大將軍韓信,還是齊王、楚王、淮陰侯,皆從來不曾如此叫喚他。
「我今日,竟到樊將軍府上拜訪。樊噲……樊噲這人,不論武功還是兵法,皆於我之下,今日我這王侯,竟落至要與這人攀交情的地步。」
「樊將軍道,我對陛下之忠日月可表,他實在不相信我會有謀反之心。他更道,朝中有妒我將才之人,要將我陷害至死……我如今已無實權,對朝中同僚根本不成威脅。莫非我韓信,當真如此令人恨之入骨……」
「那個人是你吧,劉季。天下人皆道你堂堂皇帝,妒恨我領兵之才,不惜誣衊我有謀逆之意,廢去我之王位。」
「劉季,若你真如此痛恨我,為何不早早將我處死。」
他聽得皺眉,心臟被一霎揪住的感覺使他坐於那醉酒的人旁邊,伸手攬住那肩膀,「你醉得不輕,還是早早休息罷。」
醉後的淮陰侯比往日都要誠實,誠實得讓他不由得悔恨,以如此手段散佈謠言,毀去那人於朝中的清譽,竟是在逼迫眼前之人至死地,不得翻身。
他思及往日無聊之時,捉住駐足於案上的蠅,本以為牠會於他手中掙扎亂飛,豈知當他放開了掌心,那蠅卻已靜躺於他手上動也不動,應是他手勁過大之故。
他又豈會有致他於死地之心。
那人對他的舉動未有反抗,兀自閉上眼睛,唇邊只低低吐出一句。
「我不明白你在想什麼,劉季,你到底在想什麼。」
他聞言,僅只緩緩收攏垂放於腰側的五指,將指尖握得死緊。
你不明白朕在想什麼,朕又何嘗不是。
可,即使知悉了他的心思,又能如何。大漢皇帝,終究需以鞏固大局之名,將楚王韓信迫回京師,終究,要親手將他曾經最為鍾愛的、睥睨敵軍的高傲表情硬生生扼殺。
那尊嚴被一霎褫奪的模樣是朝他刺來的青銅矛尖,銳利疼痛,被劃出的口子雖不深,卻使他不忍卒睹。
-----------------------------------------
我想這CP對部份看官來說應該是挺雷的OTZ可是沒辦法,一個月前我寫著寫著論文,翻著翻著資料就萌倒了sosad又是一對不在計劃內的CP OTZ
話說在寫這文之前,不論是校園還是歷史,寫作進度像是在HK公路堵車一樣走走停停-____-希望可藉由此文破蛋吧=v=|||(天:什麼蛋?!?)
最後,其實這是2011賀文(?)在這兒預祝看官新年快樂=v=(眾:你在下篇才說這話還來得及吧-_-)
訂閱:
發佈留言 (Atom)
Link List
Labels
- 記事/廢言 (58)
- 【校園同人】憑劵入場Serial no.U00001(關燁 X 藍琰) (17)
- 【校園同人】蹉跎(袁奉孝 X 郭浩) (16)
- 短文 (16)
- 【校園同人】都說了我不是同性戀(張班長 X 洪無丹) (11)
- 還(荊軻 X 姬丹) (8)
- 【校園同人】做人不要太變態(鍾俊彥 X 何家輝) (6)
- 甕中捉鱉(囊瓦 X 姬申) (6)
- 販售資訊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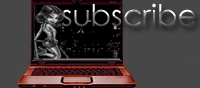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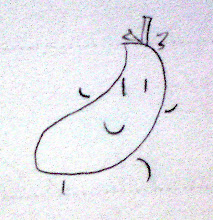


0 留言:
發佈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