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沒來由地想起他的髮妻。
他心中的妻子向來皆是如此溫柔體貼,為他料理許多許多他並不擅長之事,然自數年前開始,他的妻子的神色有那麼一點點跟以往不同,可實際上有何不同,他說不出來,只知道,妻子態度如往日一般溫婉,但又像是失卻了以往的柔媚。
他見過那臉龐失去溫柔的表情,非惡狠狠如欲奪去敵人性命的軍士,只是面上無一絲波動,所有情感都沉澱在眼眸底下,讓他捉摸不著。
以往他們居於陋室之中,那處不知為何總有青蠅盤踞,他看著妻子在房中團團轉著驅趕青蠅,最後她雙手一拍,在他目光之中停下腳步。
「捉著了。」她攤開掌心詳端,良久呼出一口氣,他瞥了一眼她手中紅黑的一抹陰影,不發一語。
營營青蠅,止於樊。
豈弟君子,無信讒言。
他聽見妻子吟誦著這麼一句,不禁問道:「青蠅與讒言有何關係?為何非得要將兩事連在一起?」
「夫君,此曲本就以蟲喻人,勸君王莫要被顛倒是非之小人所蒙蔽。」
他聞言只一皺眉頭,並無開口辯駁。小小一只昆蟲豈有顛倒是非之能耐,只不過,蠅本愛纏繞事物,在他面前盤旋一圈又一圈,他先是不耐地揮手驅逐,至後來,他心神被奪,目光定在那幾要看不見的雙翼上,忘卻了本來之正事。
如此微不足道的細節,若非他的妻子提起,他也不會想起。
數日之前,他與皇后一同晚膳。上一次與髮妻單獨進膳,似乎是很久以前的事,自他登上皇位以後,於沛縣時的日子,彷彿是數十年前的回憶,堆積成了他一頭蒼蒼白髮。
「陛下,臣妾有一事,請求陛下不吝賜教。」
他驀然抬首,朝坐在他不遠處的皇后一挑眉。當初於沛縣時他不識字,還是經她指點他才略通文墨,如今皇后,竟也有事要向他請教?
「說吧。」
「有青蠅在室內纏繞不去,陛下若在房中,會對此蠅作何處置?」
數日以來,他腦中思及皆是四方諸侯之威脅,那數位曾為他打天下的將領,他今日卻不得不將其鏟除,將其兵權收歸漢室。
「這問題,朕猜皇后早就心中有數,又何需問朕?」
皇后雖為後宮之人,但畢竟曾跟他一同討伐秦楚,對當今之局亦有所瞭解,他想,皇后亦應明瞭他言下之意,知他意指的青蠅為何人。
在他眼眸之中的皇后,艷紅的唇緩緩牽起一絲笑意,眉眼低垂。
「陛下英明,臣妾的確心中有數。」
接到臣下通報之後,他匆匆下旨回宮,繼而直奔長樂宮,門前卻只見靜靜佇立的蕭丞相,他心中一急,不由得連名帶姓地斥道:
「蕭何,你好大的膽子,竟敢未得朕旨意下輕率處置朝廷重臣?」
丞相只彎腰一揖,語氣冷靜,「陛下,臣此舉亦是奉皇后之命除害,請陛下恕罪。況且此人意圖謀反,陛下仍容他立於朝中,實在難以服眾。」
朕之命即是一切,誰敢不服?又何需服眾?他想如此大吼,但丞相此時又道:
「陛下,皇后已於宮內,恭候陛下多時。」
淮陰侯被害之事既成事實,他不能不將滿腔驚怒冷卻下來,朝丞相一拂袖,雙履跨過門檻之時,不由得回首瞄了多年來追隨他左右的大臣一眼。當年淮陰侯被他拜為大將,這得歸功於向他舉薦的蕭丞相,然如今丞相竟奉皇后之命,剷除舊日曾力薦之人,此種所謂同僚情誼,殘酷得使他齒冷。
他的淮陰侯卻從來未有加害同僚之念頭,縱然孤傲,也不屑用此種手段除去異己,失去兵權、將才無用武之地,在朝中的淮陰侯如稚兒,不詣箇中陰險。
淮陰侯醉酒當夜,他帶他往榻上歇息,正欲轉身離去,那時他突地拉住了他,力度之大讓他有些重心不穩,直撲榻邊而去,正正伏在酒氣濃重的人身上。
他側過首,碰上榻上之人的眼眸,那眸中清明不似有醉意,半晌他衣襟被一手扯住,鼻尖撞上優美的鼻樑。他鼻腔有些疼痛,唇上卻是帶著酒香的甜,被吸吮繼而以舌尖撬開的嘴唇被熱意帶動,薰得他忘了要撐起雙臂離開床榻,將這副身軀遠離他指尖觸及之處,只記得自己曾是在如此氣味之下,將他最鍾愛的將軍困在牆壁間親吻,而他的將軍為何未有反抗,他不知道。
他隱隱盼望淮陰侯神智清醒,卻又忐忑於他酒醒時的反應,只是他與他的舉動如野獸互相侵略掠奪,反倒使他的神智開始宛若醉酒一般昏沈起來,如他每一個夢中,對他的淮陰侯予取予求。
薄汗在他額際凝聚,埋首於那彷彿微赧的耳廓之時,他聽見耳邊一句微嗄低語。
「我如此信任你,劉季,你為何不信任我……」
他怎會不信任他,他又怎忍心不相信他,那話語似是再次捅穿他心房外那片肌膚,搗出一縷一縷鮮紅,那道深可見骨的血口,他雖未有親眼察看,但他知道,已是血肉模糊。
刺痛愈加劇烈,將他緊緊纏繞,於夢中追隨不捨,他也不願丟棄,只由它盤踞於腦海心臟之中,慢慢腐朽侵蝕著他,如此,這感覺便只屬他一人所有,再也無人能與他爭奪。
在他意料之外,他最想要獨佔的東西,終究為人所奪去,而那對手,竟是他的髮妻,他聽著皇后看似冠冕堂皇的理由,一瞬間,連開口說話的能力也被奪走,全無聲色。
「臣妾不過是鏟除於室內死纏不休之青蠅,陛下曾謂,此事應當如何辦,臣妾心中有數。陛下莫非,將此事忘了?」
他固然記得他曾如此說過。
可那青蠅,怎會跟他話中所指的,大相逕庭。
「臣妾以為,淮陰侯一直對陛下不服,日前又與叛將陳豨合謀,如此下去,淮陰侯舉兵叛變,乃遲早之事……臣妾只不過,圖個以防萬一。」
他呆怔立在原地良久,忽爾扯出淺淺一笑,縱然他相信他,又有何用,堂堂大漢皇帝,竟然不敵後宮婦人之手段。
「……朕要見他全屍。」
皇后楞了一下,迅即回道,「回陛下,臣妾下令處斬淮陰侯之後,已命人將其梟首。」
宮中一片宛若被烈火吞噬過後遺下敗瓦頹垣的靜謐,他無視皇后訝異的目光,冉冉拖著步子踏出宮門,在門外向一直待命的丞相,艱難地吐出一句命令。
※ ※ ※
呂雉端坐於案前,指甲深深陷進皮肉之中,待殿門前足音響起,她驀地抬起頭,話語掩不住滿心焦慮。
「為何不見留侯?本宮不是命你傳召留侯入宮嗎?」
進殿使者低首一揖,「回皇后,微臣方才拜訪留侯,留侯並未在府上,故未能為皇后召留侯入宮,請皇后恕罪。」
呂雉怔怔看著那神色未變的使者半晌,方揮手要他退下,站起身於殿前踱著步,繞出了一個又一個弧線。
牙齒幾要咬得格格作響。
她幾日以來不斷傳召留侯,然不知那留侯究竟是有心還是無意,每一次她遣使者到他府上,皆是不見人影,要她所派的使者空手而回。
近來兩手手心不時冒出冷汗,她無一刻不在算計著日子,聽聞姓戚那賤人日夜於陛下榻前又哭又鬧,陛下如此寵愛那賤人,早晚會答允她之要求。
若然那雜種真取代她盈兒之位,不止她后位不保,依那賤人之性子,或許更會以計取她性命……
這大漢江山,陛下取之不易,而她為陛下髮妻,皇后之位若被他人所奪,她跟隨陛下這數十年,豈不是白白糟蹋了?
陛下對她早已失卻所有感情,她從來都明瞭,單憑一已之言,加上自己為后之身份,陛下必會認為她失寵成妒,因而中傷那賤人,如此她后位更是朝不保夕。
她只能想到,若是往日與陛下情同手足之功臣向其進諫,說明廢立太子之害,陛下應會放棄改立那個雜種的念頭。她本打算向蕭相國求援,然近日蕭相國似乎亦為自己強買民田之事分身不暇,且相國身份亦不便對此事加以插手。
而功臣之中,從不過問政事、亦鮮有入朝之人只數留侯,若留侯願助她一道,她或能避過一劫。
但她亦明白,縱然留侯向陛下進諫,也非絕對能夠成功,畢竟多年過後,陛下性子愈發難以捉摸,也愈加喜怒無常。而自去年開始,陛下更是經常行蹤不明,有時她以為陛下是到姓戚那賤人的寢殿去,卻偏有心腹向她通報,道陛下出宮去了。
呂雉眉心緊鎖,好半天後揚手召來心腹,命道:
「明日再往留侯府上一趟。切記本宮如今所作之事,萬莫讓陛下知悉。」
※ ※ ※
漢十一年春,淮陰侯韓信謀反關中,夷三族。十二年,高祖罷黥布軍歸,民道遮行,上書言相國強賤買民田宅數千人。高祖至,何謁。民所上書皆以與何,曰:「君自謝民」。後何為民請曰「願令民得入田,毋收稿為獸食」。高祖大怒,乃下何廷尉,械繫之。
城中有淮陰侯故宅,二更有一人循巷而入,夜夜如是。人皆以為有盜,遂上報內史,然終不了了之。
-----------------------------------------
史實中上面那段是黃昏+忘年戀(?)不過就請看官們忽略掉這個事實吧=v=||||||回想起之前那篇論文,我把政治制度寫成了將軍被殺的根本原因,不然皇帝其實沒有必要將他趕盡殺絕的sosad
最後還要多說一次:看官們合皮扭耳:):):):)
訂閱:
發佈留言 (Atom)
Link List
Labels
- 記事/廢言 (58)
- 【校園同人】憑劵入場Serial no.U00001(關燁 X 藍琰) (17)
- 【校園同人】蹉跎(袁奉孝 X 郭浩) (16)
- 短文 (16)
- 【校園同人】都說了我不是同性戀(張班長 X 洪無丹) (11)
- 還(荊軻 X 姬丹) (8)
- 【校園同人】做人不要太變態(鍾俊彥 X 何家輝) (6)
- 甕中捉鱉(囊瓦 X 姬申) (6)
- 販售資訊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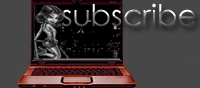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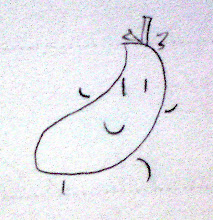


0 留言:
發佈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