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子眾富戶自此經常邀他為客,讓他在大廳中恣意擊筑,而他每酒過三巡後起身告辭,抱筑回到老丈人之宅,房門邊總會有一道踡曲而坐的影子,繼而在月光下迅速站起。
「你再如此下去,秦皇帝會下令追捕你的!」
他正要推門而入,聽見少主的話後立在原地,轉首凝睇他。少主眼中充滿責備之色,然在責備之下,那擔憂不安的情愫,赤裸裸呈現在他目光中。
「少主,自我身份暴露人前那日起,我已不怕秦皇帝會將我送至咸陽。」他微微一笑,又轉身步入客舍。「我本已無懼一死,又豈會受秦皇帝之令所嚇?」
「但是我怕。」
少主驀地吐出一句,他微怔,後即欲關上房門將那話語隔絕於外,少主卻一腳踏進舍中,雙手按住他肩膀逼迫他與他對視。
「我曾謂不會讓你涉險於外,然而最終我卻失信於你。每一回你外出作客,我都無法肯定,此次你出門以後,還會否回來?抑或是被朝廷之人捉拿到咸陽?」
「我無法掌握你的行蹤,也不應限制你往外作客……我只是,想圖個安心。」
手中之筑愈顯沉重,他眼前,儼然倒映著數年前的自己,大驚失色看著故人執拾包袱準備遠行,明知伊人將隨時涉至水之湄而離去,他仍執意扯住那人衣袖,因他知道,此回一別,他將無從尋回這位故人與之相見。
「少主,」他乾澀的嗓音在靜謐的房中響起,「請你明白……我早晚,也會離開此地。」
他肩上的雙手倏然收緊,少主一楞,迅即回道:「不論你要到何地,我都會隨你而去。」
那臉上的神色很是堅決,他只能報以苦笑,一路走來,他太清楚這種執迷將為少主帶來何種後果,若不及時勸止,只怕少主會成為第二個高漸離。
「少主上有高堂,且尚未娶妻,如此四處飄泊恐怕不妥。」
「我意已決,若你真要離開,我亦只好有負於爹娘──」
「為人子女,豈能如此不孝!」他聞言忍不住揚高嗓音,卻被少主一語駁回。
「你如此不顧自己性命,難道你就無負於父母了嗎?」
他安靜下來凝視他,反倒是少主在吼完以後即露出歉疚的表情,壓低了聲音:
「……抱歉。我不應如此待你……但我實在,無法忍受你隨時離我而去……」
若是無法忍受,就裝作輕鬆無懼,如他於易水畔無言擊筑,心裏告訴自己,伊人非他所能挽留,在伊人渡河以後失去蹤影,他也只求能在遠處張望,再看那人一眼。
可惜少主似乎未能明白,在秦皇帝之詔傳來之時,他平靜回舍收拾行裝,直至有人猛地打開舍門。
他沒有回過頭去,俐落把手中布袱打了個結,冷不防腰際纏上一雙手臂,使他忍不住皺眉,輕輕掙動要擺脫那雙手,身後之人卻像是無意放開。
「別去,漸離,別去。」
少主哀求的聲音鑽進耳中,數年前的景象彷如重現,只是少主成了當時的高漸離,而他,則成了那個一去不還的刺客荊軻。
此世間,只需要一個執迷不悟的高漸離,他無法容許有第二個同樣執著的人的出現,因為此種執著,足以誤人一生。
「少主,你明知我必將赴咸陽,而秦皇帝之詔,亦無人能抗。」
他嗓音冷淡,如今他必須使少主面對現實,無以改變的事實曾給予他痛楚,但他相信,此乃令少主放棄的必要方法。
「少主,若你能及時放手,終有一日你將慶幸,當時你作出了正確的選擇。」
放開了雙手,對伊人獨自渡河視若無睹,多年過後回想此事,便能暗自慶幸自己當日的冷靜理智,不至於使自身落得不堪之境地。
他也曾有過如此機會,但他當時並未放在心上,直至他不由自主涉水而行時,他仍不能明瞭,自己本應留在岸上靜渡寒暑,伊人只不過,乃一名遲早離岸遠去的過路人。
可他依然循著故人的步伐來到咸陽,晉見那使他和故人不得相見的秦皇帝,然後在皇帝侍臣一道耳語下,被押進了一間正生著爐火的密室。
先是一股溫熱的感覺,伴隨而來的刺痛逐漸擴大,四肢被牢牢鎖上銬鐐使他無法掙扎,只得緊咬下唇抵抗痛楚,劇疼帶來了無比清晰的認知,認知勾出了他深藏在眼眶的清淚,口腔倒灌的血液腥鹹中,眼淚被蒸發得毫無痕跡。
眼睛往後,再也不能帶領他往那熟悉的水邊,而待他再回到水中摸索尋途,伊人已走得太遠。
他在原處,捻弦以竹牘擊出一曲,以十指探索一段時日過後,雙手雙耳比往日更敏銳,宛若要聽見岸邊寒風吹過,捲起水中無數波光的微響。
筑音從商變為角聲,他不禁屏住氣息,抿唇凝神,所謂伊人,正於彼岸踏著纖弱帶霜的蒹葭,冉冉踱至水邊,每一足音,皆鼓動他期待已久的心房跳動,撫筑掌指幾要輕顫起來。
溯游從之,宛在水中央。
「陛下小心!」
他猛地雙掌一翻,巨響震斷了河水,蒹葭上的白露微晃跌落草叢中,他向後仰倒,灌進岸上的水流彷彿浸濕了他的髮。
在水一方伊人停佇,他在另一方微笑著,感受點點溫熱如和煦暖陽,噴濺到他臉上。
訂閱:
發佈留言 (Atom)
Link List
Labels
- 記事/廢言 (58)
- 【校園同人】憑劵入場Serial no.U00001(關燁 X 藍琰) (17)
- 【校園同人】蹉跎(袁奉孝 X 郭浩) (16)
- 短文 (16)
- 【校園同人】都說了我不是同性戀(張班長 X 洪無丹) (11)
- 還(荊軻 X 姬丹) (8)
- 【校園同人】做人不要太變態(鍾俊彥 X 何家輝) (6)
- 甕中捉鱉(囊瓦 X 姬申) (6)
- 販售資訊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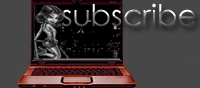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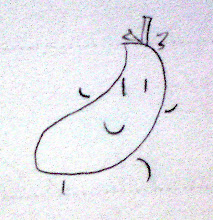


0 留言:
發佈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