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荊兄,是次入秦,可有歸期?」
他深知,其實他不需多此一問。這位故人素來言出必行,今既是不欲再等待前輩入燕,又何以談歸燕之期。
荊兄從來不曾顧慮,他這名一直視他為至交的友人。
他恨迫荊兄赴死的太子丹,卻更恨荊兄為了太子一言,便要衝動入秦,就算賠上性命也在所不惜。
消息傳至薊都之時,他在城郊林間,尋得了一樹下的草叢,以鐵鋤翻開深埋叢中的軟泥。
棕紅的泥土暴露在翠綠叢間,不知何來的執念讓他放下鐵鋤,雙手探進泥中緩緩撥出狹隘的洞口,泥中碎石割開他手掌的肌膚,他卻彷彿再也感覺不了痛,任赤色隱進軟泥,逐漸形成一足以放進一布袱的洞穴。
捧起一旁堆疊的數件衣衫,他猶豫半晌,最終慢慢擱進那洞穴之中,撫摸那疊在最上頭的藍衣的動作,宛如當夜他髮上所得到的觸感。
我此生最快意之事,荊兄曾道,莫過於認識了賢弟你。
他只能報以無奈微笑,認識了此人,他才明白,原來自己亦不能免俗,擊筑之時傾聽那人放歌,便能使他感到愉悅,甚至為此種愉快的感覺,特意另造一音色更佳的筑,以助此故人之興。
荊兄曾道,他乃他的知音,如伯牙之遇子期。
在荊兄堅決要離開薊都之時,他曾想過,若他這名子期開口挽留,伯牙是否就會願意在薊多等待一段日子,但是那結果讓他失望。
一切皆在他意料之中,知音又如何,對荊兄而言,高漸離不足以成為他停留下來的理由。
他抱來一旁的筑,徐徐將那筑放在衣物旁邊,木然盯視半晌,始撥來軟泥,讓屬於荊兄的一切淹沒土下。泥上豎立的木牘一片空白,秦王已下令搜捕刺客荊軻之黨羽,在牘上留字徒為秦軍留下自身蹤跡。
秦王搜捕刺客黨羽之時,秦軍亦已直撲燕國,以燕軍之勢,根本不足以抵抗如狼似虎的秦國大軍。
薊都將要淪陷之際,他僅能連夜趕往鄰國,遠離故鄉非他所願,然此途乃他暫保性命的唯一辦法,未達成目的前,他不願令自己每日皆冒被秦軍認出身份之險。
他只等待一個時機,以圓他一直以來的執念,哪怕那機會如佼人在水之涘,他亦將循道而尋。
※ ※ ※
「此調既有善,亦有不善。」
筑上竹牘一頓,擊筑人抬起了頭,黑亮的眸子直視他,他垂首急步而過,不由得懊惱自己經常不假思索衝口而出的惡習。
此戶之少主亦是愛擊筑之人,每逢聽到筑音中有錯調,他總無法忍受地皺起眉,身為擊筑者,豈能如此不慎。
然與此同時,看著少主坐於堂上擊筑,他便想起往日酒後放歌的荊兄,以及,那個微笑以筑音和歌的自己。
「你究竟是何人?」
「回少主,小人自小父母雙亡,自是無名無姓。」
「我不相信你。」
少主的敏銳起初令他有些不知所措,生於富戶,這少主能有這般洞察力實是難得。
每日於宅中如其他奴僕一般作粗活,五年以來,未有不適應之感,夜晚四下皆靜之時,他便觸摸那被布帛包裹五年不曾取出的筑,指尖下微凸的弦被布緊束得無法捻動分毫。
有時他會將筑擱放在陋室暗處,單是撫摸不能再讓他捻弦輕敲的筑,便能憶起那閉目而歌的臉,幾要令他拋開現下安穩日子,溯洄從之,在岸邊某處來回找尋,這渴望使他覺得,太過可怕。
他為尋伊人而來,在水中失足而溺,死前猶能見那人在水中沚,他也能微笑瞑目。
「高漸離。」
他聽而不聞,手中掃帚頓住,抬起左手手背印著額上滲出的汗水。一人閃至他面前,伸手拿走他手中的掃帚。
他慌忙後退一步,瞪目看著少主如洞悉了一切般續道:
「你就是五年前,燕國刺客荊軻的黨羽高漸離。從你一開始來此處為庸,我便已觀察著你。你一言一行全然不似那些無名小輩,且比我更精於音律,我就知道,你極可能是一知音人。」
身份被揭,他暗藏忐忑心音,開口婉道:「少主過獎了,小人豈會是那高漸離……」
少主卻彷若未聞,眼睛瞬也不瞬地凝視他,「高漸離,秦王已併天下,若使他得悉你匿於宋子,他必取你性命。」
他抿唇與他對視,少主眼中堅定已不容他否定事實,清朗眉目本應使不少姑娘對其青睞有加,然他想起,自三年前少主回絕丈人娶妻之要求,如今已過了娶妻之齡,而老丈人已久未過問。
「秦皇帝曾謂,生擒高漸離者,得黃金二千鎰。」他平靜啟口,唇邊綻出淡笑,彷彿已無所懼。「少主若要得秦皇帝之賞,大可將我送抵咸陽。」
「我已告知我爹,從今以後你便是我一人之僕,無人會得知你的身份。」少主沉道,那話語著實出乎他意料之外:「我不會讓你涉險於外。」
雖說少主之話不在他預料之中,但他並非不能明白。尤其是,每逢他應少主之求奏畢一曲,那彷彿藏有深意的說話,在他心房外小心翼翼敲著門。
「能有你一知音,我此生已別無所求。」
他僅能回以一笑,輕輕掙開那執起他雙手的掌心。知音知音,他也曾為得一知音而暗喜於心,後來卻是不滿於荊兄只待他如良朋的事實,再後來,是同樣為他知己的人一去不返以後,他在水邊踟躕,終發現自己除了那人,已一無所有。
少主的感覺,他也曾有過,僅一次的不慎失足,使他終生不得抽離其中,感受著冰冷徹骨的河水沖刷衣襬,同時張望岸邊,總相信在彼岸草叢間,必有那人的蹤影。
「少主,擊筑雖好,畢竟此非公子人家所學,何苦終日沉迷?」
「可是我喜歡。」
少主手握竹牘抬首看向他,那目光太坦率不加掩飾,只能由他無語別過視線,因他了解,若他給予他回應,少主或只會愈陷愈深。
當老丈人揭破他身份時,他暗自鬆一口氣。老丈人將他當成座上客,也不再讓他跟在少主身旁,免除了他和少主必須日夜相處的尷尬局面。
他執牘的手靜止在半空,抬眼之時,滿廳賓客以袖拭淚的情景使他不禁愕然,環顧四周之中,一雙冷靜與他相望的眼睛分外銳利。
猶如不容他再閃爍躲避,但他最終仍是,故作視而不見。
----------------------------------------
這是目前為止自己寫得最滿意的唯一一篇文sosad悲哀的是這文主要寫高美人單戀不止,更是BE lollol
訂閱:
發佈留言 (Atom)
Link List
Labels
- 記事/廢言 (58)
- 【校園同人】憑劵入場Serial no.U00001(關燁 X 藍琰) (17)
- 【校園同人】蹉跎(袁奉孝 X 郭浩) (16)
- 短文 (16)
- 【校園同人】都說了我不是同性戀(張班長 X 洪無丹) (11)
- 還(荊軻 X 姬丹) (8)
- 【校園同人】做人不要太變態(鍾俊彥 X 何家輝) (6)
- 甕中捉鱉(囊瓦 X 姬申) (6)
- 販售資訊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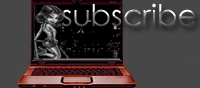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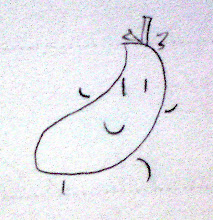


0 留言:
發佈留言